宁宗一 | 性:美好和邪恶的双刃剑
小编 2023年2月15日 17:00:03 小说大全 236
历史久远的沉默,往往是一种久远的期待,期待着公平、客观的认知和耐心的品味。
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在他那部《生活的艺术》一书的自序中,列举了十来位他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上杰出的人物的名字。
他赞扬这些人,“全是不依传统的人,这些人因为具着太多的见解,对一切事物具着太深的感觉,所以不能得到正统派批评家的喜悦,这些人因为太好了,
所以不能遵守‘道德’,因为太有道德了,所以在儒家的眼中是不‘好’的”①。
我不知道林先生是有意回避那位更富有“独立见解”、更具有挑战性的人物——兰陵笑笑生,还是同样漠视这位小说巨擘的巨大存在。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笑笑生要比林先生提到的涨潮更“感觉敏锐”、更“熟悉事故”;比袁中郎更“戏谑诙谐、独出心裁”,即同样“不依传统”,而富有
更强的叛逆性。令人遗憾的是,早在1937年林先生做出的预言,在他提到的人物画廊中,确实在今天一个一个地开始被证实又都成为现实。
而兰陵笑笑生和他那部给他招来无穷灾难的《金瓶梅》,却始终不为更多的人认同,笑笑生仍然是一个“孤独者”,一个被看作是“另类”的人物,他的书
还被一禁再禁,一删再删!

《金瓶梅》
展开全文
如果你打开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的《金瓶梅》第一页,就会赫赫然看到纯阳真人的七绝:
二八佳人体似酥,
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
暗里教君骨髓枯。
这是“色箴”,还是“色戒”? 不过我们却惊奇地发现,这首诗和以后写男女交欢的很多诗一样,都像是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厮杀! 这就又和房中书的告
诫完全相反了。
“金瓶梅世界”令人瞠目的是,人人色胆包天,个个淫心炽盛。 性行为已成了一种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日常活动。
对于小说主人公西门庆来说,处理公务家事和应酬宾客中的片刻空闲、午睡醒来的困懒、浇完花木后的无聊等等,性行为都成了他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
的享乐方式。
小说另一位主角潘金莲日日把拦着汉子,仍不满足她的性要求,间或还要拿琴童和陈经济来解渴。
李瓶儿好风月,对蒋竹山不满的原因之一也是蒋竹山满足不了她的性欲。 而春梅也因淫欲过度,得了“骨蒸痨”,最后死在了姘夫的怀中!
主子不分男女都无节制地性放纵,奴才中通奸偷情的事也是连绵不断。 书童与玉箫、玳安与小玉、来兴与如意儿等等,都在释放他(她)们的“性压
抑”。
综观《金瓶梅》全书的每一处性描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传统小说中常见的情爱与美感的因素已经完全被排除在外。 但现在的关键是“性”描写并不
可怕,问题倒是以什么笔法来描写。
《金瓶梅》的性描写的最大特点是露骨,即直接的、不加掩饰的、毫不含蓄地写性交场景和诸多细节,这就成了批评者反复批评的“秽笔”,也是《金瓶
梅》在各个时期被删被禁的根本原因。
我们通常看到的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金瓶梅词话》删去了19161字; 齐鲁书社1987年版的《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删去了10385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本的《金瓶梅词话》删去的字数较少,但也是把特别露骨的性交场面和“秽笔”删去了四千多字,而对描摹
性情景的词曲则大部分给予了保留;
作家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卜键《双舸榭重校评批〈金瓶梅〉》,删去性描写三千字,这是迄今我们看到的“通行本”删去字数最少的一部了。
但是,人们要问,性,真的是洪水猛兽吗? 性描写,在“金瓶梅世界”真的是多余的“秽笔”吗?
对此,可以见仁见智,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又确实存在,即我们即使阅读删得非常干净的“洁本”,只要是一位认真的读者也都会感到“性”在全书
中如幽灵一样无处不在,它融入到小说描写的所有日常生活和细节刻画之中。
性心理、性情趣、性话语也几乎渗透于各个人物和情节之中,这一切是我们在阅读《金瓶梅》时无法回避的一个大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从这部小说的整体艺术结构来看,笑笑生对性交场面的安排,比如详略、显隐、疏密、冷热,似乎都有所考虑。
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西门庆生活中的最大的享乐方式和最大乐趣,性活动始终是和他的其他贪欲的追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同样被纳入到由盛到衰的
总体趋势之中,这一点就显得很重要了,因为它们既有渲染色情的效果,但也可能或就是另有寓意了。 这是“金瓶梅世界”的一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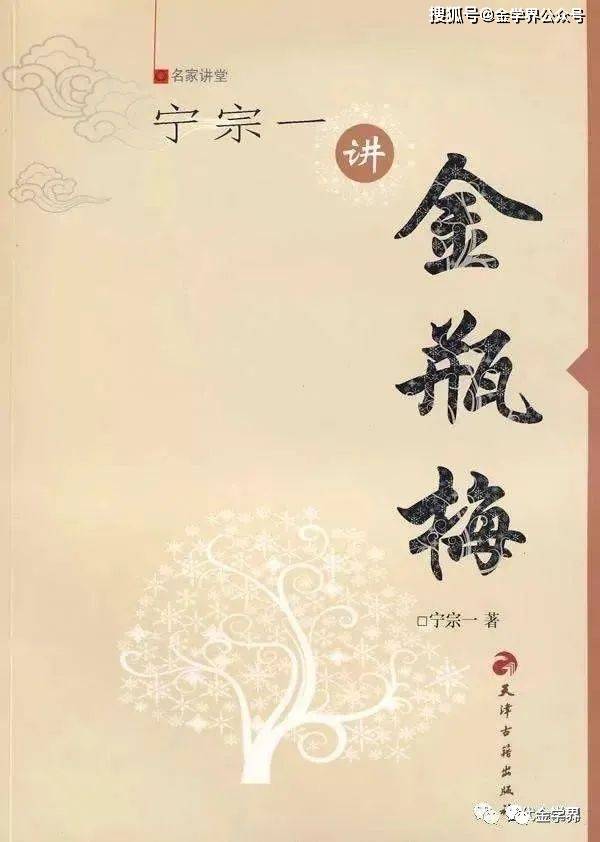
《宁宗一讲金瓶梅》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在西门庆的成群妻妾中,很必然地产生一种性氛围,一种有时看得见、有时看不见的那种性竞争的“场”。
一人竟拥有六个固定的女人,外面还有颇具威胁性的对手,这就必然形成性竞争。在“金瓶梅世界”中潘金莲就扮演着这样一个最活跃也最露骨的角色。笑
笑生针对这种情况发表了他的意见:
看官听说,世上妇人,眼里火的极多。随你甚贤惠妇人,男子汉娶小,说不嗔,及到其间,见汉子往他房里同床共枕,欢乐去了,虽故性儿好煞,也有几分
脸酸心歹。
事实上,在“金瓶梅世界”中,我们分明看到了那热火朝天的争夺男人的拼搏。 在性竞争中,有的人丢了面子,有的人挨了打,有的人甚至连命都送掉。
主子内部如此,参与这种性竞争的还有奴才和伙计的老婆,如王六儿、贲四嫂、来旺媳妇等;除此之外就是更有色与欲实力的妓女,如李桂姐、郑爱月儿等
一批女人。
三种势力,有分有合,有打有拉,于是“金瓶梅世界”给你展示的除“性”以外,其背后就是“利”的交易了。
比如西门庆一贯在枕席间同他的女人们搞肉体和财物的交易。或为了奖励这个女人“枕上好风月”,立刻就交付一件价值不菲的衣服。
比如王六儿满足西门庆性的怪癖时,就可以得到她想要的财物。就是在这些性描写中,我们的作者如此巧妙地把男人的好色与女人的贪财并置在一起。
这种设色布局大大冲淡了性交描写的刺激效果,而让人们感受到女人为了“物”而供他人享用的悲哀。这就是绣像本《金瓶梅》的评点者所说的那句名言:
以金莲之取索一物,但乘欢乐之际开口,可悲可叹。
另外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王六儿和西门庆的私通。王六儿在获得性满足时也获得了财物的满足。只是一切都在性交过程中,这倒也是令人匪夷所思了。
总之,从王六儿和如意儿一直到非常霸道的潘金莲,几乎都是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换取钱财或地位的工具。
妙不可言的是,这些女人在和西门庆进行性交以后,作者就会很仔细很耐心地记录西门庆付给她们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首饰、多少银两。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性交易的关系并非是阳具,并非是春药,而是实实在在的钱与物。
对这样的叙述和描写,我们怎么能简单地说笑笑生只是单纯地写或庸俗地欣赏呢?
还是 聂绀弩 先生说得好,他认为笑笑生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写性并不是不讲分寸,他是“把没有灵魂的事写到没有灵魂的人身上” ① 。
从道理上讲,文学作品中描写性爱,就不可避免接触到自然的、社会的和审美的三个层次,纯生理性的描写,往往容易堕入庸俗污秽的色情,而社会性的
描写则是有一定意义的,《金瓶梅》的性描写,我认为属于第二层次,它唯一的缺陷,就是没作第三层面的审美的处理,或者说它还没有把这三个层次结合得完
美, 中外文学名著中,都不乏因“性”的描写而引起的纷扰,以致有打不完的笔墨官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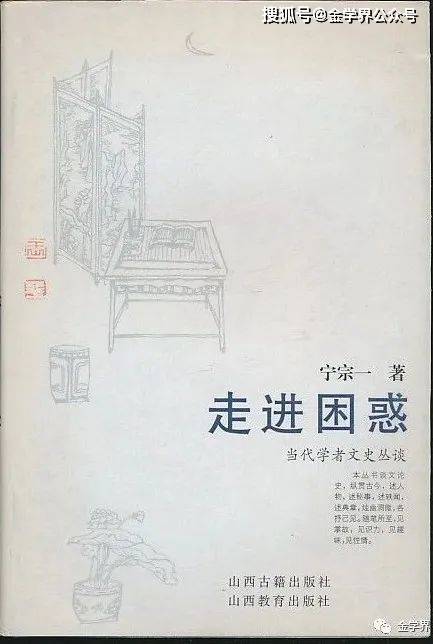
《走进困惑》 宁宗一 著
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一些研究《金瓶梅》的学者,又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把《十日谈》和《 查泰莱 夫人的情人》进行比较。 而这种比较研究似乎无
不立足于几部书都有较多的性的描写。
其实这是一种误读。 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之间的可比性并不大,且不说社会背景、文化走向不同,就是几部书的主旨也大相径庭,因为它们的美学前提
就是不同的。
《十日谈》中的一百个故事,内容是很驳杂的,而且良莠不齐。 但总体倾向则是贯穿着强烈的反宗教、反教会、反禁欲主义的精神。
如前所述,一方面是因为刚从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中冲出来,物极必反,难免由“禁欲”而到“颂欲”; 另一方面却也是市民资产阶级的爱好,但归根结
底是对伪善而且为非作歹的教会、邪恶好色的神父、嫉妒成性的丈夫进行揭露、讽刺和批判。
然而,《金瓶梅》则与此迥然不同。 笑笑生笔下的小说主人公西门庆是个泼皮流氓,是个政治上、经济上的暴发户,也是个占有狂(占有权势、占有金
钱、占有女人),理所当然地从他身上看不到丝毫的“精神吸引力”,也不存在具有“精神吸引力”的真正爱情。
道理是如此简单,西门庆与他的妻妾之间和情妇之间,连起码的忠贞也没有。
进一步说,《金瓶梅》从来不是一部谈情说爱的“爱情小说”,如果用爱情小说的标准来要求它,那简直是天大的误会。 当然,它也不是以后出现的“才
子佳人”小说。 如果说它是“秽书”,那就是因为笑笑生从没打算写一部“干净”的爱情小说,他可不是写爱情故事的圣手!
所以他也不可能像真正的爱情小说那样,在性的描写中,肉的展示有灵的支撑,也就不存在本能的表现必须在审美的光照下完成。 所以它只能处于形而
下而不可能向形而上提升。
因为他承担的使命只是宣判西门庆的罪行,所以他才写出了一个代表黑暗时代精神的占有狂的毁灭史。
因此,用“爱情与色情”这一对命题去评价《十日谈》与《金瓶梅》,是无法真正看到《金瓶梅》的价值的。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但“奇”在哪里? 有的研究者就断言: 作者用了那么多的笔墨,对两性生活作了那样淋漓尽致的铺陈,这不是唯一恐怕也
是重要的原因。
不错,有的读者对《金瓶梅》就是抱有“神秘感”“好奇感”,而其所“感”,可能包括对其中两性生活的描写的猎奇心理。 但是如果《金瓶梅》的本质
和特点仅止于对性和性行为的直露描写,这种“神秘感”“好奇感”以及带来的轰动与喧哗只能是短暂的一瞬,因为它可以被更有“神秘感”的黄色书刊代替。
而事实是,从这部小说于16世纪末问世以来直到现在,世界各国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对它的热情一直未减。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证实了一个问题,这部小说的意义远不是由于它的对性的描写,而是它的真正属于文艺的价值,是这部小说的故事、人物所包含
的丰富的社会内容使它具有弥久不衰的魅力。
也有的研究者认为《 查泰莱 夫人的情人》是一部好书,《金瓶梅》是一部不道德的书,因为《 查泰莱 夫人的情人》是从女性的角度、以女性为本位
的,它和《金瓶梅》那种以男子的性狂暴为本位的描写完全不同,它是对女人的敬意、一种对性的尊重。 我觉得这种说法同样是对两部名著的误读。
在我看来,劳伦斯主观上绝对没有以女性为本位的思想,他明明标出了男子和女子都能自由地、纯正地思想有关性的行为。
其次,我们不妨引用作品的具体陈述来加以印证。 该书第十四章麦勒斯向康妮回忆他和他原妻白莎·库茨的性关系。 他们之间的性关系是地道的以白莎·库
茨为本位的,而结果是给麦勒斯带来无尽的痛苦。
由此可以看出,劳伦斯写这部小说从来没有划分以女性为本位和以男性为本位以及孰优孰劣的问题。
事实证明,以女性为本位和以男性为本位都是片面的。 对于性来说,只能是以男性与女性的共同和谐为最高标准。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闻一多先生在《艾青和田间》一文中的一句话,他说: 一切价值都在比较上看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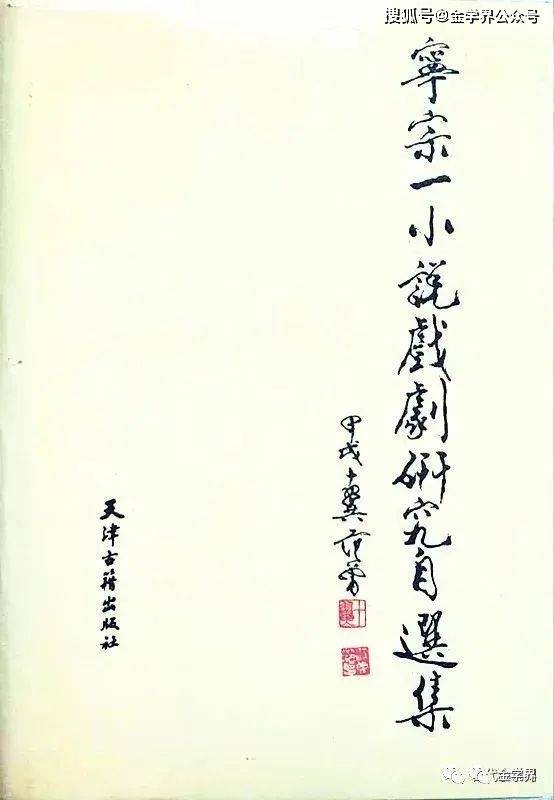
《宁宗一小说戏剧研究自选集》
但是,比较绝不是简单地扬此抑彼,而是为了作出科学的价值判断。
我认为《金瓶梅》不应成为人们比较研究的陪衬和反衬或是垫脚石。 把它置于“反面教材”的位子上进行任何比较,都是不公平的。
下面我想正面地谈谈我对“金瓶梅世界”中性描写的意义以及我们应有的价值尺度。
从《金瓶梅》的全部内容来观照,我们既看到了裙袂飘飘,也看到了佩剑闪亮。 这场关于情欲的奇异之旅在语言的纠缠里达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西门庆对潘金莲、李瓶儿和王六儿等的性爱是疯狂的,更是毁灭性的。 这也许正暗含了不朽之经典所能具备的元素。
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性”是一把美好和邪恶的双刃剑。而将“性”沦为卑下抑或上升到崇高,既取决于作家也取决于读者的审美与德性。
说句实在话,围绕《金瓶梅》中的“性”人们已经说了几百年(是不是还要说下去?)但是,当我们把这个问题置于人性和人文情怀中时,对它的解读就
真的会是另一种面貌了。
人们认为最羞耻、去极力隐讳的东西,其实恰恰是最不值以为耻、去隐讳的东西。大家以为是私情的东西,其实也正是人所共知的寻常事。
真正的私情的东西恰恰是每个具体人的内心感情和心灵体验,那是最个性化的、最秘而不宣的东西。
而事实上,历史的行程已走到了今天,性对人们而言已失去了它的神秘性、隐讳性。人们在闲谈中带些性的内容,都已变成司空见惯的了。
但是,谁又会将心灵深处和感情隐秘一一流露和轻易告之他人呢?为什么对性,就不能以平常心对待呢?性,不需要任何理由,它只是存在着。
在我们以往对《金瓶梅》的解读中,对性的态度与行为往往是一种道德评判的标准,其实,这对于小说的本质而言是徒劳的。小说最应该表现也难以表现
的是人的复杂的感情世界和游移不定的心态。
人的道德自律在于要正视纯粹、自然和真诚。评论界开始明智地指出:劳伦斯将性的负面变为正值。公然提出性就是美,并把笔下的主人公的性关系以浪
漫的诗意来表现。
而像已故的青年作家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对以往的道貌岸然的反讽中,将性价值全然中立化,他让人们在净化中理解两性关系的意义,于平淡中体味
人的温情,人性之美自然溢出。我当然理解,笑笑生不是劳伦斯、王小波;《金瓶梅》也非《 查泰莱 夫人的情人》和《黄金时代》。
我只是希望我们从中能得到这样的基本启示:在未来的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将性的价值尽量中立化;在净化中理解两性关系的意义,并以平常心对待,这
也许会变得可能。
现在我们把话题再拉回到《金瓶梅》文本中的性描写,这里我想引用当代著名作家阿城在他的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中的两段话,作为我们思考该问题的参考:
《金瓶梅》历代被禁是因为其中的性行为描写,可我们若仔细看,就知道如果将小说里所有的性行为段落摘掉,小说竟毫发无伤。
“潘金莲大闹葡萄架”应该是兰陵笑笑生的,写的环境有作用,人物有情绪变化过程,是发展合理的邪性事儿,所以是小说笔法②。
《宁宗一研究精选集》封面
注释:
①聂绀弩《谈〈金瓶梅〉》,读书,1984年第4期。
②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
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后收入《宁宗一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转发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