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花月夜》:孤篇岂能压全唐
小编 2022年4月18日 07:44:28 小说大全 280
由于王闿运(1833-1916)的“孤篇横绝”(后演义成“孤篇压全唐”或“孤篇盖全唐”)和闻一多(1899-1946)的“诗中的诗,顶峰中的顶峰”的高度赞赏,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下简称“春”)为近现代特别是当代所追捧。加上大众传媒电视的推波助澜,《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全唐” 俨然成为了“共识”。
《春江花月夜》果真可以压全唐吗?
一
来看一看“春”自唐有唐诗选集以降,它在各种选本或全集中的命运和地位。
据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的《唐人选唐诗新编》,所列唐人选唐诗,共录唐人选唐诗16种。16种无一有选“春”的。唐末五代后蜀韦榖所选编印的《才调集》,是宋之前唐诗选本所选唐诗最多的一部,《才调集》“自叙”称“今纂诸家歌诗,总一千首”。再从唐人最先的唐诗选本看,也不见“春”的踪迹。《河岳英灵集》共选诗人二十四家、诗二百三十七首。据傅璇琮考,《河岳英灵集》选编者殷璠系润州人即今江苏镇江人,与包融为大同乡(今江苏丹阳)。包融、贺知章、张旭、张若虚世称“吴中四士”(《全唐诗》张若虚条,郑振铎称“吴中四杰”)。包融、贺知章、张旭的诗见唐人唐诗选本,但唯独不见张若虚。在《国秀集》(所选诗人九十家、诗二百二十首)的“自序”里,选编者芮挺章说“昔陆平原之论文,曰‘诗缘情而绮糜’。是彩色相宜,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谓也”。拿这一标准来看,“春”是符合的。但《国秀集》没有“春”的影子,倒录有刘希夷三首五言。佚名所编的《搜玉小集》,不仅录有刘希夷五言歌行一首七言歌行两首,其中《代白头吟》中的“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何其相似。刘、张同为吴中四杰,为什么唐人选唐诗会厚此薄彼呢?显然,“春”不入选者法眼。即便“春”符合唐人“彩色相宜、烟霞交映、风流婉丽”的这一种鉴赏标准。唐末五代的韦庄选编的《又玄集》里,对所选诗人及诗有一个标准即“入华林而珠树非多,阅众籁而紫箫唯一”。“春”之“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符合这一标准,但《又玄集》录唐诗人一百五十人诗三百首(案,此为“唐诗三百首”的祖师爷),也没有“春”的踪影。
唐、五代过了来到了宋。宋又是如何对待“春”的呢?
宋代最先的也最有名之一的唐诗选本当数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唐百家诗选》录诗人一百八(一说一百四)、录诗一千二百四十六(一说一千二百六十二),没有张若虚,却录有刘希夷九首,其中就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此诗已从唐人选唐诗的《搜玉小集》的《代白头吟》更名为《代悲白头翁》(自此便以此定名,从《唐百家诗选》到《唐诗纪事》直到清的《唐诗别裁集》和《全唐诗》)。王荆公在其自序里讲,“欲知唐诗者,观此足也”。尽管选集没选李杜(当时李、杜也有专集印行传世),尽管清人对此说大不以为然,但“春”未能入选,可见宋人的态度。这一态度延续到两宋之间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唐诗纪事》共录唐诗人一千一百五十家。《唐诗纪事》是明代《唐音统签》之前集唐诗最全最多的一部唐诗全集。这一唐诗全集,没有张若虚,当然也就没有了《春江花月夜》。在卷第十七贺知章一节里,计有功引《旧唐书/贺知章传》写道:“神龙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文词俊秀,各闻上京”。并说若虚为“衮州兵曹”。计有功此说(案,实为《旧唐书》之说),恐为诗史上第一次记录了张若虚及张诗的存在和风格。“春”首次录入,是宋郭茂倩选编的《乐府诗集/清商曲辞》。自此,《春江花月夜》才登上了中国文学史、中国诗史的历史舞台。
宋过了,来到元。《唐才子传》大约成书于元大德八年(1304年),为中国诗史第一部唐诗人的传纪。据傅璇琮等校笺《唐才子传》称,《唐才子传》录诗人278、附传 120,合计近400人。包融、贺知章、张旭、张若虚,在《唐才子传》里什么情况呢?包融(卷二)、贺知章(卷三)有专传,无张旭传,在李白传里有“白益傲放,与贺之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饮酒八仙人’”。“吴中四士”在《唐才子传》,独没有张若虚名字。“春”虽已在《乐府诗集》出现,但依然没有得到当时的看重。元的历史很短,不到一百年,这便来到了明。在明一代,明初明末有两部唐诗汇编印行。明初高棅编的《唐诗品汇》,明末胡震亨编的《唐音统签》。《唐诗品汇》以其“文章高下”将所录唐诗分为九“品”即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等。《唐诗品汇》卷第三十七录有“春”,但列入最末一品“旁流”。在高棅眼里,“春”与“正宗”“大家”“名家”等品比,是上不了台面的。称作在清《全唐诗》之前最全的唐诗集《唐音统签》中,也难觅张若虚。《唐音统签》共设十签计一千二十四卷。其中乙(79卷)、丙(125卷)、丁(341卷)、戊(201卷)签分别为初、盛、中、晚唐诗共七百四十六卷。张若虚大约生活在初盛唐之间,但乙签、丙签均未录有张若虚。在录有“乐章”(10卷)、“杂曲”(5卷)等的辛签里,也没有《春江花月夜》。“春”会跑到哪里了呢?
从明来到了清。在清一代,虽非汉人执掌大宝,却是一个整理汉籍最昌盛的朝代。仅唐诗一门,不同选本和全集,应有尽有。清初王夫之的《唐诗评选》对“春”算得上情深。王写道:“句句翻新,千条一缕,以动古今人心脾,灵愚共识。”王夫之作为一位苛儒一词压两宋,对过往人物,向来否多于臧。却评“春”时给予了前世从未有过的赞许。这为后来雍正年间印行的《古唐诗合解》提供了关于“春”的鉴赏新视野。清中期有了集大成的《全唐诗》(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选集《唐诗别裁集》(康熙五十六年1717)和《唐诗三百首》(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全唐诗》卷轶浩繁,近五万首,大约是为唐诗留下所有血脉与毛发(案,后来从敦煌石室、从海外特别是从日本发现的唐诗未进入这个全集),或许是供专家们使用的,自然有《春江花月夜》。沈德潜个人独立完成的《唐诗别裁集》选唐诗近两千,两千首不选“春”,恐难尽理。但最为普及的《唐诗三百首》,“春”未能入选。或许在蘅塘退士看来,“春”是入不了唐诗精华三百首队列的。即便对“春”依然不屑,但清与唐宋明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前有王夫之,在后有王尧衢。前王前已述,后王编著的《古唐诗合解》(此为集选本、诗话、鉴赏为一体的唐诗选集),在逐句解读“春”之后,王总结道:“情文相生,各各呈艳,光怪陆离,不可端倪,真奇制也”。这一评价,开创了对“春”有始以来的最高评价,也为王闿运、闻一多对“春”无比艳羡提供了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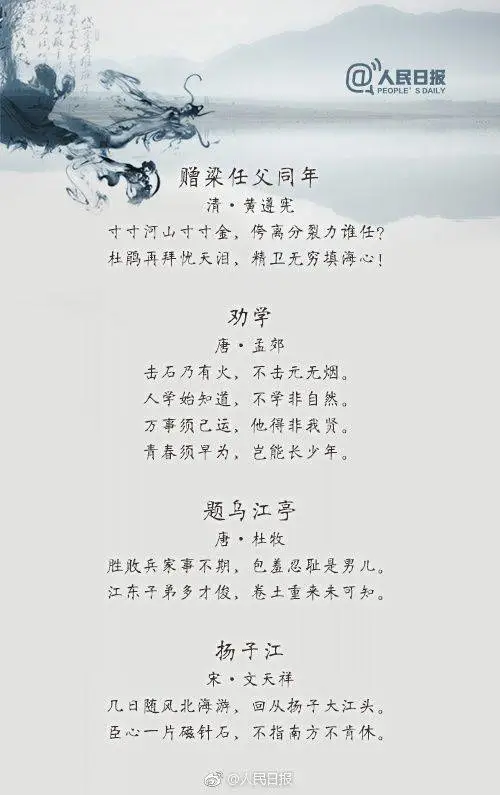
到了这时,王闿运、闻一多仍然不是诗史或唐诗鉴赏的主流。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是中国近现代第一部诗史。成书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中国诗史》,第二章“初唐诗人”一章里,著者一没有专门列举张若虚,二引诗时也不举证“春”。只是在这章的结尾时写道“四杰沈宋以外,加上上官仪、杨师道、刘希夷、张若虚等风格也相近,我们就无暇细述”。印行于三十年代的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十五章写道“若虚……所做《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的一首七言的长篇,乃是令人讽吟不能去口的隽什”。现代最早之一的“中国诗史”和“中国文学史”,事实上对“春”也仅是泛泛而论。到了1964年,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为高校文科编的专业中国文学史教材《中国文学史》,对“春”的评价似乎比郑振铎还不如。游等认为,《春江花月夜》,虽然“意境和情趣完全不同”,但它毕竟是“游子思妇”的传统的题目和题材;虽然“诗中想象时间的永恒,空间的无限,对当时读者是有启示性的”,但是“这里也有怅惘低沉的感伤”。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何至于此?
二
这涉及到唐诗鉴赏的流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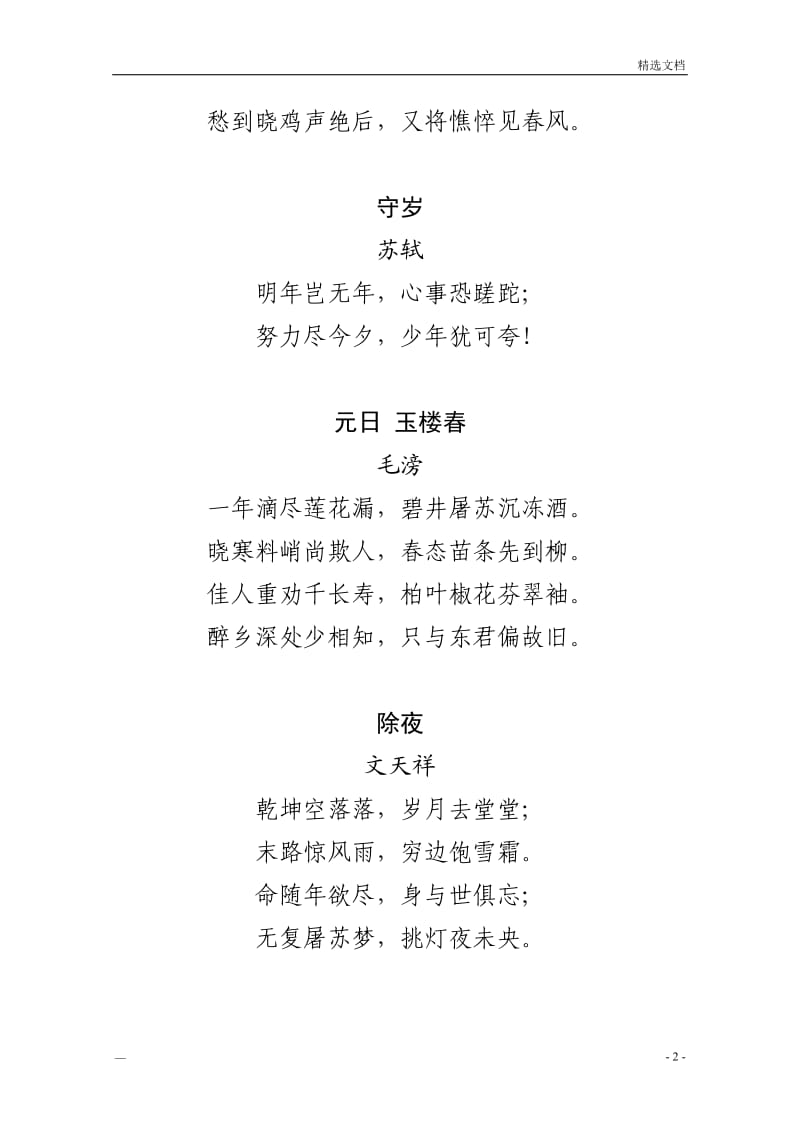
诗话,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从孔颖达的《毛诗正义》起,诗话的历史悠久如天地玄黄。与唐诗几乎一起生长的唐诗诗话,以及历代诗话,从中古史的唐宋到近古史明清,一直延绵到近世,而且还决定了诗的发展、诗论(鉴赏)流变与不同时代的趣味。在海量的诗话中,稍作梳理,我们就可以看到《春江花月夜》在这些诗话里的地位、分量和唐诗鉴赏所呈现的不同面相。
众所周知,唐诗以初唐四杰(王杨卢骆)开其端。但是,初唐四杰诗风所带有“徐庾余风”则在当时就受人诟病。陈子昂横空出世时,陈的朋友卢藏用说陈诗为“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所谓“质文一变”,就是彻底与六朝诗风告别。从而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从来没有过、在后难以为继的“唐诗时代”。关于“徐庾余风”,事实上,包括初唐四杰已经有足够的清醒。杨炯在为《王勃集》作序时说王诗“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又说王诗“长风一振,众萌自偃”。可见杨炯的诗观,已经与六朝诗风划清了界线。这为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唐诗重要一脉拉开了帷幕。张若虚生活的年代正与陈子昂(张岁还比陈岁长)生活的年代重叠。陈能在中国诗史上留下“唐诗诗祖”(元人方回语)的地位。作为诗人张若虚,仅在《旧唐书/贺知章传》里露面。“春”作为诗文本,在唐渺无诗迹,到了宋才见诸诗界。何以如此,因为自陈诗始,诗“始归雅正,李杜以下,咸推宗之”(《全唐诗/陈子昂条》)。
唐诗进入盛唐,诗家蜂起、诗风纷纭,而李杜两家突兀群山、领袖群伦,则是唐诗乃至中国诗史最重要的事件。关于李杜,从来就是众星捧月,也从来就是诗话的主角。中唐诗人的韩愈、元稹,可能是最先把李杜连在一起来谈的重量级人物。韩愈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元稹进一步将李杜同论。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里,元讲:“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之谓‘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一词压两宋,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显然,元稹更看重杜甫。看重杜甫,不仅在唐一代、在宋、在明都沿袭了这一传统。也有例外。《河岳英灵集》共选诗人二十三家,有李白无杜甫。在李白小传里,唐人殷璠称李“率皆纵逸”“奇之又奇”。
李杜并论,兼论其他,是中国诗话的主脉和重要内容。兼论他家,为何“春”不入唐宋法眼?开诗论先河的晚唐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说:“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渟蓄、温雅,皆在其间矣。然直指所得,以格自奇。”司空图举例如“得于江南,则有‘戍鼓和潮暗,航灯照岛幽。’又‘曲塘春尽雨,方响夜深船’”。司空图关于江南诗鉴赏,不举“春”而自举,大约也没把“春”放在眼里。《诗品》其二十四品,就“春”来说,如冲淡、纤秾、洗炼、绮丽、清奇、旷达、形容、飘逸等大都可以沾得上,郭绍虞的《诗品集解》,引古人注读《诗品》时,没用“春”举过证。如“冲淡”,郭集《皋兰课业本原解》说“此格陶元亮居其最。唐人如王维、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亦为近之”;如“绮丽”,郭集引《皋兰课业本原解》说,“此言富贵,出于天然……如入园林,百卉向荣,自有生意,即如老杜所云”;如“形容”,郭集《皋兰课业本原解》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摩诘兼擅,故而著名。若李杜之诗,不但画家圣手,而且几于化工之肖物矣。”几乎可以说,“春”在唐、宋、明,或许从来就没有进入过诗话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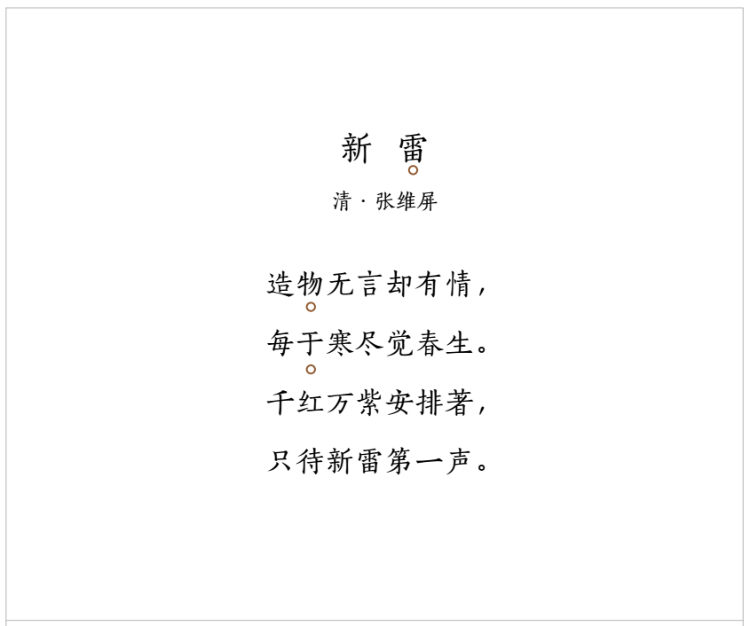
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最能表明这一态势。《沧浪诗话》第一章“诗辨”里,严为好诗定调:“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而尽而意无穷”。就这一好诗标准,严在“诗评”一章里又补充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这样的诗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春”虽有“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的元素,但却不在严所论之中。因为,“春江花月夜”这一宫体是南朝陈后主与宫女及朝臣间的相和与采艳而作,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这一脉的遗脂遗粉。即便它拉开了与宫体诗的距离,但在崇杜的两宋,怎么可能入得了诗史与诗话的正脉?
如果说唐人司家图的《诗品》简明扼要地总结了唐诗及之前诗歌的二十四种主要风格,那么宋人严沧浪的诗话则是对唐诗最为系统 也最为开放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史。严之前的欧阳修、姜夔、黄庭坚等都李杜并论但崇杜为首,宋有“千家注杜”即可表明。黄彻的《巩溪诗话》在比较李杜时,黄说“如论其文章豪逸,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比较杜白时,黄说“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难”。李杜并论、崇杜为首的传统到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明初的宋濂在《答章秀才论诗书》虽然没有忘记赞扬李白“其格极高”且“神龙之不可羁”,但论杜则写道:“杜子美复继出,上薄风、雅,下该沈、宋,才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真所谓集大成者,而诸作皆废矣”。至于其他,家家都有瑕疵。王(维)“虽运词清雅,而萎靡少风骨”、元(稹)白(居易)“近于轻俗”、韩(愈)柳(完元)“晚自成家”、温(庭筠)李(商隐)“专夸靡蔓”等等。明末的胡震亨在《唐音统签/癸签》比较李杜时写道:“太白诗闲适,游览居多,罕及时事,安能如杜诗一一得其岁月次第之?”。高濂的“诸作皆废”,遑论《春江花月夜》!屠隆在《鸿苞集》以“三宝”给诗排行:三百篇是如来祖师、十九首是大乘菩萨、杜少陵是如来总持弟子、李白是散仙、温飞卿是野狐禅等,这一“排行榜”,哪有张若虚的名份!
清代,是诗话极为繁荣的时代(也是诗话终结的时代)。王夫之等开其头,翁方纲等垫其尾。清诗话,虽然一如宋明崇杜尊李,但兼论诸家且杜也非独尊。相较于宋明诗话,这是清诗话最明显的变化。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说“子美早年未醇处,从阴铿、何逊来,向后脱卸乃尽,岂黄鲁直所知耶?” 袁枚更直接“余不喜黄山谷诗”(这为后人钱锺书讨厌黄诗提前伏笔。顺便说一句,钱的《谈艺录》里也无“春”的影子),而且对王安石更是一笔横扫。《随园诗话》卷六开头就说:“王荆公论诗,开口就错”。众人所知,把杜甫抬到神的地位的主要肇事者就是黄庭坚。王夫之对黄庭坚的“清算”,也就是从杜诗处开始反省。黄说杜诗“无一字无来处”,汪师韩在《诗学纂闻》“杜诗字句之疵”节里指出“诗到少陵,谓集大成者,然不必无一字一句之可议也。”严廷中更严厉:“宋人诗话,宗韩祖杜,令人生厌。黄彻《巩溪诗话》尊工部而抑太白,更为呓语”。宋人当然并非都如此。朱熹对李杜就较中庸。于李,《朱子语类》说“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于杜,“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渐放手”。徐增《而庵诗话》倒还中正:“诗总不离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
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维摩诘。太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随园诗话》为清代诗话的翘楚之一,袁枚不再执着于李杜,对唐诗有了更宽泛的认知。袁说“各人性之所近”,如“杜甫长于言情,李白不能也”。以杜律为圭臬,袁以为不齿:“余雅不喜杜少陵《秋兴八首》……此八首,不过一时兴到语耳,非其至者也”。在清一代,眼界更为开阔的当数王渔洋的《师友诗传录》。如:王问其友、徒唐人有无五古一事。阮亭答:“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三家,横绝万古”;萧亭答:“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沈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微,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参岑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师友诗传录》不仅在清一代诗话举足轻重,也是中国诗话最重要的论著之一。王渔洋,作为清一代最杰出的诗界领袖,博识灼见,且《师友诗传录》又为多人的唱和与论辩,反映出清代诗话的重要变化。尽管清代贡献了两部历史上最好的杜诗全笺注即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和杨伦的《杜诗镜铨》。但清诗话打破杜诗独尊或者打破只论李、杜、白、王等成为某种共识。这样,其他诗才有了空间;这样,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才得以浮出水面。
三
回到王尧衢、王闿运和闻一多对“春”的抬举。
前已述,王尧衢在《古唐诗合解》里称“春”是“奇制”,为王闿运的“孤篇横绝”提供了脚本。那么“孤篇横绝”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标识的呢?王闿运在《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完夫问〉》中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李贺、商隐挹其鲜润;宋词、元诗尽其支流,宫体之巨澜也。”这段话有两关键词,一“横绝”,一“宫体”。“横绝”一词并非王创。在以“诗话”作为中国文学理论的第一部诗话《六一诗话》里,宋人欧阳修说“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师友诗传录》说“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三家,横绝万古”;“横绝”一词用于李、杜、王至理,用于张若虚名不符实。二、“春”从宫体诗中走出,让“春江花月夜”这一清商调焕然一新,这当然是张若虚的功绩。但毕竟它还是宫体,顶多是宫体的“巨澜”或者是宫体的“孤篇”而已。王闿运的“孤篇横绝”(演义或讹变为“孤篇压全唐”),实在给诗史开玩笑;今人喜引闻一多“春”为唐诗“顶峰”,更是断章取义。闻在《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一开始就说“宫体诗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春”有了“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至于一百年间梁、陈、隋、唐四代宫廷所遗下的那份最黑暗的罪孽,有了《春江花月夜》这样一首宫体诗,不也就洗净了吗?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张若虚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这一段话是《宫体诗的自赎》一文的末段。这段话十分清楚明白:“春”,一是完成了对浓脂腻粉宫体诗的救赎;二是为即将到来的盛唐诗风与陈子昂一起开通了道路。所谓“诗中的诗”即是“宫体诗中的诗”,所谓“顶峰上的顶峰”是“宫体诗上的顶峰”。一首《春江花月夜》,实现的只是宫体诗的救赎,它哪里可以压全唐?陈寅恪评价柳如是写《春江花月夜》,就是“效温飞卿之艳体”(《柳如是别传/第三章》)。陈说亦可旁证“春江花月夜”这一宫体的趣味和价值。
如果不是清一代诸贤打破了李杜神话和杜诗独尊、拓展了唐诗的鉴赏空间,哪有“春”的出头之日?
“春”为今人追捧,除上述唐诗鉴赏流变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现代音乐的出现。琵琶曲《春江花月夜》是一首古曲,大约明末清初已经存在。十九世纪西洋音乐传入中国,由琵琶曲到管弦曲的《春江花月夜》应运而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春”在大上海华丽上演,“春”的乐曲,由此弥漫时空。乐曲的灵感源于“春”,但音乐却扩大了原诗的接受空间,“春”,由此通过音乐雅俗共赏。《春江花月夜》是否真具有闻一多所说的“宇宙意识”,于诗的鉴赏来说,仁智各见;“盖全唐”一说则是以讹传讹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