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小说20家”之八:陈宏伟研究
小编 2023年1月25日 20:16:03 小说大全 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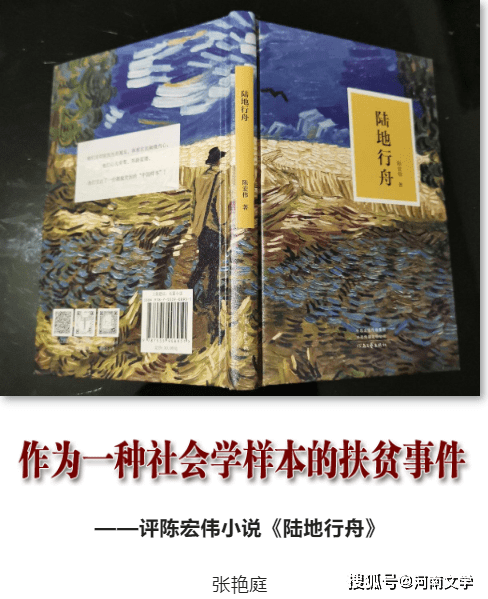
作为一部直面当下现实的文学作品,《陆地行舟》通过主人公郁洋的扶贫经历和见闻,书写了精准扶贫这一宏大的社会事件。这种对时事现实的近距离书写,很容易导致小说成为对政策的图解,造成人的消隐。而《陆地行舟》以独特的问题意识,通过对人物复杂心理世界的塑造,从宏大的社会行动深入到人内心的幽微,将诸多的社会矛盾冲突转化为人物思想层面的冲突、情感方面的冲突以及行动层面的冲突。通过对这些冲突产生与消解的叙述,作者不仅呈现出一个复杂立体的人物形象,而且进行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分析与社会反思。
展开全文
社会学家米德将人的自我区分为主我和宾我,宾我是作为社会角色的自我,按照“有意义的他人和整个共同体的观点来设想和认识自我,它反映了法律、道德及共同体的组织规范和期望。”而“人格(自我)乃是一个‘主我’与‘宾我’不断互动的过程”。
《陆地行舟》中,人物都以自我的社会身份和角色来行事。根据社会分层理论,社会中的人物必然地被分配在不同的阶层。而小说中的社会阶层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作为帮扶者的公务员群体,另一个是作为帮扶对象的贫困农民群体。作为帮扶者的公务员,需要遵循公务员体系的规则,也要将其内化为自我处事的规则,成为一种内在性的知识。伯格指出,内化是在对社会客观事件的意义进行理解、解释和传达的过程中发生的。而“所谓传达意义,指的是他人主观过程的显现。”
《陆地行舟》采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事,也就是内聚焦的叙事形式,使主人公郁洋成为小说中唯一可以呈现其主观世界的人物。我们可以把握郁洋的主观世界,从而看到郁洋将外部标准内化的过程。伯格指出:“只有在认同发生的情况下,内化才能发生。”小说多次写到郁洋默背工作相关的数字,他对这一行为的解释是:“工作干得好不好,情况吃得准不准,就看数字记得牢不牢。”郁洋对之认同的原因是:“想想看,如果在会议上面对领导的提问时,能说出一连串数字,甚至包括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必然震惊四座!”
社会学家韦伯认为,科层制所推崇的是工具理性,而数字化正是工具理性也是技术理性最重要的表现。对背诵数字的推崇,其根本原因是对科层制本身的认同。郁洋在小说中也表露了自己想要在科层体系中晋升的愿望,称其为:“挑重担”。在这种认同之下,郁洋的宾我严格遵守科层制的相关规范。这种遵守与迎合也不仅局限于工作的数字化等显性规则。对于共同体内的潜规则也遵守并迎合。如在《隐山茶叶志》中,他放弃副主编的署名权;张根财的蓄水塔被偷他也选择不报警。原因都是不想给领导惹麻烦,影响其在领导心中的形象,从而影响其升迁。
这些显性规则和潜规则都是构建其社会性自我即宾我的内容。而郁洋的这些行动,可以理解为他的主我对宾我的顺从和认同。但与此同时,郁洋的主我却又时时在内心里矫正自己的宾我。如面对复杂的乡村现实,他在心里感叹:“农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他们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每一个人都有好恶、有爱恨,有内心的矛盾、冲突和忧伤。”
这种以自我为镜像来理解他人的思维方式,是其主我的体现。但这种思维方式在工作中,在具体行动中,却屡遭挫折,导致了自我认同的危机。这种自我认同的危机,也是一种身份认同的危机。身份认同可以说是主我对宾我的认同,但又不仅仅是对具体社会角色的认同,更是对一种共同体以及制度秩序的认同。作者在《镜中之舞》这一章中,呈现了共同体内部的道德问题,问题的产生恰恰是为了维护制度秩序。这种制度秩序与道德冲突为郁洋带来了身份认同的危机。
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其实在每一章中都有所呈现。米德的自我理论认为,主我可以对宾我进行反思。在宾我的压抑下,郁洋的主我反思方式最后只剩下了隐喻和反讽:陆地行舟的隐喻,孤独城堡的隐喻,“人物”的反讽。如果说前两章的隐喻指向了外在世界,指向了社会现实,那么反讽则不仅仅是指向外在的社会,还指向了自我。因为对人物论的反讽不仅指向了科层制中的等级制度,并将讽刺扩展至科层制中的人,即制度中的共同体。这共同体中的人不仅包括李北亚,还有那些为“人物论”鼓掌的人。郁洋作为共同体中的一员,也包括在其中。这种反讽也是主人公主我与宾我同一化的最后尝试。因为反讽将之前的问题化和反思性进行了消解。如果说之前郁洋主我与宾我的矛盾是进行意义的争夺,那么最后郁洋只能以反讽来完成对意义的消解,来取消这种意义争夺,从而使自我达到同一。这种意义的消解既指向外部世界,也指向自我的内部世界。这种意义的自我消解,是一个人主体性的消解,宾我对主我吞噬,然后主我与宾我在意义上同归于尽。最后郁洋的自我只残留下了一个反讽的态度,成为他能为自我的同一化所寻找到的位置。

郁洋在小说中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在庞大的理性组织之中,压抑个人的情感、想法、冲动,进而与理性组织保持一致。这在卡尔·曼海姆看来,是一种自我理性化的努力。在小说中可以多次看到他压抑自己心中的愤怒。胡组长对孙桂英家一事的的张冠李戴,让他感到“极为恼火”,面对王区长却不得不压抑自己心中的愤怒,继续去完善那些形式工作。
郁洋不仅压抑自己的愤怒,也压抑自己的悲伤。他在看到马忠良重新搭建的蛇王庙时,“心里泛起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悲伤。”但这种悲伤,他也只能默默在心中平息,而无法做出任何帮助马忠良的行动。而在第三章李北亚诬陷他时,他也对李北亚拍了桌子,但对他行为的描述却是“顿时失态”。作为小说中唯一进行内聚焦的人物,这可以看作郁洋的观察者自我对行动者自我的反思性评价。后来李北亚面露微笑,而郁洋感觉“真是肺都要气炸了”之时,却再无下文。个人的情绪在庞大理性组织的程序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他通过理性思考,觉得不应参与其中,而是服从庞大理性组织的安排。即使他看到这安排是如何地荒唐。郁洋的这种自我理性化,反而使他离真正的自由越来越远,不仅不敢做想做的事,甚至表达情感的自由也丧失了。
合理化甚至理性也并未真正带来自由。郁洋的行为不仅受束缚,他的内心也无法获得自由。小说书写了两种不同的行动。一种为情感行动,另一种为目的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行动。这两种行动之间屡屡发生冲突。小说在《台风过境》一章开头就写到了郁洋压抑情绪和情感的工作习惯:“每次遇到火急火燎的忙乱之事,郁洋都会暗告自己多几分从容和淡定,只要按捺住焦虑不安的情绪,相信一切都可以掌控。”这段话描述了郁洋的感觉结构,小说通过具体的事件呈现了郁洋的这一感觉结构。小说紧接着写了郁洋对数字的认同,但随后就写到了一个颇具象征性的情景:“默记的时候,郁洋大脑就有点迷糊,慢慢两眼睁不开了,顺势躺倒入睡。”
郁洋的入睡是一种倦怠状态的象征。这种倦怠,是人面对数字等工具理性内容时,所产生的一种状态。因为数字化本身就是一个去个性化的过程,当数字成为目的而不是手段,那么数字背后的人便被忽略。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连接感是人自我的一种重要的心理需求,只有和他人产生真正的心理连接,人的自我才是完整的,也具有更大的心理能量。因此,郁洋的倦怠可以看作是心理能量匮乏的一种象征。在科层制内部之中,他无法与人完成这种连接。《台风过境》这一章中,与他产生最直接关系的人是检查组长胡建华。他们更多是科层制中上下级的关系。郁洋只记得胡组长,而忘记他的本名,就代表了两者之间纯粹的层级性。在这种层级关系中,郁洋始终处在一种压迫感中:虽有“气得浑身战栗”的辩解,却依然被以“审贼似的目光”来对待;郁洋也将胡组长眼中的自己总结为“卑鄙”二字。这样一种压迫性的关系一直存在于二人的交集之中。胡组长对形式的过分看重与强调,呈现了科层制对工具理性及合理化的注重。而在这种程序的合理性框架之内,却不能保证真理、正义等价值理性。胡建华对合理性有着过分的追求,却对村民叫妈的行为进行了误识,偏离了事实真相,冤枉了工作人员。在这期间郁洋的主动性遭受严重的挫折:被误解,被批评,被强迫。这种目的合理性行动与情感行动的矛盾,呈现了他的情感被严重压抑的状态。
在第三章中,小说的主题也从关于组织机制社会行动的外在隐喻而逐渐转向了人的主题。对“人物”一词的反讽性运用,即是对于人的异化的反讽。在李北亚的“人物论”中,人的价值被分层,但在道德层面上,社会地位和价值高的人,却并不一定有比地位低的人更有道德,甚至更为低下。制造“人物论”的李北亚就是其典型代表。李北亚作为一个专家知识分子,“学者型的文化局长”,也把自己的聪明用于拍马屁,用于出卖诬陷朋友和编造谎言,欺骗公众。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异化。而这种异化不仅发生在李北亚身上,也进一步延伸到了那些赞同“人物论”,并为之鼓掌的隐山区干部身上。而郁洋压抑自己的愤怒,并找渠道消解它们,对李北亚敬而远之,也是面对这种异化的一种消极抵抗。但这种消极抵抗,却无法改变他本身异化的事实。
人是文学进行社会分析和社会批判的起点,因为人的思想、行为甚至情感都是由具体的社会环境形塑而成的。正如《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所说:“人(humanness)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变量,换句话说,并不存在一种来自稳定的生物学基质、能够决定社会—文化变异的人性(human nature)。”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对人性困境的揭示,其实也就是对社化—文化问题的揭示。
“人物”论,即是一种社会分层论。分层即意味着社会所建构的等级体系。对人物论的质疑,就是社会分层的质疑,剥去了“人物”的光环,同时也解构了“人才”的价值。反讽不仅指向这种社会分层,而且指向了科层制,因为等级性正是科层制的重要特征。
科层制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在科层制共同体内部是行之有效的,但小说书写了一种双重空间,即科层制空间和乡村空间。扶贫将这两种空间或共同体体系连接起来。原本在科层制共同体内部行之有效的逻辑,在乡村空间中,却是失效的。工具理性的失效进一步凸显了帮扶者行为的可笑。不仅如此,如果说第二章主要书写了科层制中工具理性的失效,那么第三章中,则是写到了科层制内部道德的失效。而道德的失效,则进一步凸显了人异化的实质。
米尔斯认为:“理性组织是一个使人异化的组织”。韦伯也认为,人类的合理化进程却无法保证给人带来意义与价值,相反,合理化的机制反而可能成为人的囚笼。而《陆地行舟》中对人的异化的书写,更具体地体现了这一反思。
社会控制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是社会之所以存在的基础,“指的是社会迫使桀骜不驯的人回归既定轨道的各种手段。”社会控制的手段丰富多样,而权力手段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米尔斯认为:“现在,广为盛行的权力手段是管理与操纵人们的同意的权利。郁洋在小说中遭遇多处不公。从《隐山茶叶志》署名,到被胡组长冤枉不能申冤,到成果被李北亚利用,每次郁洋只能被动接受。每一处不得不同意,就可见权力操控的痕迹。
而对于小说中的另一群体,贫困农民则呈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小说中真正的弱者是贫困农民。弱者在这种权力关系中,大多是顺从的。孙连发面对郁洋的帮扶,就没有提自己能力的有限性,而是同意进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郁洋这样一个机制内部的低权力者,在面对另一阶层时,却又成了一个高权力者。这种权力转化与社会分层密切相关,从中可以看出权力的流动性特征。正是因为这种流动性,它几乎可以无所不在,相应的操作也无处不在。
在斯科特《弱者的武器》一书中,作者认为装呆卖傻也是弱者最常用的一种武器。这种武器集中体现在张根财身上。张根财向郁洋表露出憨傻的一面,但却隐瞒种瓜一事及其收入,为的是不影响其贫困户身份。小说中郁洋对之也有察觉:“这使郁洋轻吁一口气,再朴实的农民其实也有狡黠的一面。”这种表面顺从背后的狡黠就是一种弱者的武器。但小说中弱者并未一味地以顺从和狡黠等为武器,马忠良就是最典型的代表。马忠良所反抗的主要是村干部为主导的权力。他的一意孤行甚至超越了弱者的武器的范畴。所以郁洋才在小说中将他称为“牛人”。黑格尔将人类的冲突概括为一种争取承认的斗争。马忠良在小说中,即是在争取一种承认,对他付出劳动的承认。这种争取承认的斗争中,马忠良不顾一切。所以最后获得了郁洋的认可和尊重。事实上,孙连发宁愿累死也要串完珠子,也是在争取一种承认,即让帮扶者或官方认为他可以自食其力,也是有价值的。
小说中社会冲突的无所不在,表达了作者社会冲突合理性的观念。因为每个人都在进行争取承认和尊严的斗争。其实连瑞也是在实行一种弱者的反抗,其消极怠工和搞男女关系也是因为争取承认斗争的失败。在这种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弱者的身份也是流动的,而这种斗争也会始终持续的。
社会控制的方式,不仅有权力手段,还有其他丰富的手段。在《陆地行舟》中,还体现在对赠与原则的使用上。社会学家莫斯提出礼物理论,认为赠与和还礼是一个根本性的社会原理,“赠与物包含‘灵’和‘心意(人格)’,而接受方则受还礼义务的心理性约束。”根据莫斯的理论,赠与原则并不受经济原理和制度的限制。
朱主任在马鞍村的行为,屡次触犯村民的尊严和正当权利,才会引发村民与他的冲突。泄露村民儿子疾病的秘密,所以招致村民的殴打;他发放外国奶粉,也招致村民的怨言。但是朱主任并未理解。他所秉持的态度仍然是一种作为社会文化的“赠与”原则。在赠与原则中,被赠与者有回礼的义务。即使不是一种物质的回礼,也要回以精神性的礼,即感谢和赞美。以这样一种作为社会无意识的赠与原则来思考,他的火冒三丈也就合逻辑的。事实上他的赠与奶粉行为,正是中了消费主义圈套。正如那个年轻媳妇所说,厂家无偿赠送奶粉,是为了让婴儿产生依赖然后再让消费者购买。而消费者购买的价格中,就隐含了那些赠送奶粉的价值。但这并不是朱主任的阴谋,而是一种消费主义阴谋。但朱主任却无意之中将赠与原则与这种消费主义阴谋相捏合,显示了朱主任的脱离现实,也使社会控制变得复杂化。从此可以看出,小说不仅书写了公务员扶贫者和贫困农民两个场域,还涉及到消费主义作为主导规则的场域。多个场域及其规则引发了冲突,在这种多重冲突中,底层农民的权利和利益最终受到了损害。而争取权利与尊严的斗争在这种复杂的思想环境下,也会不断变更面貌。

社会冲突是现代社会学关注的一个焦点。社会学家达伦道夫认为,社会冲突无法避免,在任何社会中都无时不在。齐美尔等社会学家则指出冲突的积极的一面,认为其是最具活力的互动和交往形式。《陆地行舟》聚焦于社会冲突过程的书写,但小说中的社会冲突的结局,并非对社会冲突中问题的解决,而是对冲突中问题的掩盖。于是表面上冲突解决了,但问题却仍然存在。体现在小说的叙事层面,则是小说的叙事闭合完成,意义闭合却无法完成。
《陆地行舟》开头第一句话,即颇具象征性地写到了小说的关键词:“好几次都虚惊一场。”虚惊就是小说的一个关键词,暗示了冲突的解决。一般意义上来说,所有小说都必须解决矛盾冲突,才能够完成叙事闭合。但使矛盾冲突消失的方法,不仅有解决,还有掩盖。不管是解决还是掩盖,都能够促成一种叙事闭合。叙事闭合更高的层面是意义的闭合。小说《陆地行舟》中的叙事闭合,并未导致意义闭合。反倒凸显了意义冲突。因为这种意义层面的闭合并未完成,意义冲突也始终存在,因此,这种“惊”并未被化解成为虚惊,而是始终存在,成为一种社会现实中的震惊,这种“惊”也成为对社会现实一种最严厉的拷问。海德格尔在阐释人的存在问题时,指出应以存在代替存在者,意在揭示人的存在并非是静态固化的存在,而始终是一种情绪的绽出与流动。小说中,惊成为一种最重要的情绪,人卡顿在这一时刻,成为对社会现实最重要的反应。本雅明也认为,震惊是不容易被化解的。人无法顺利地将之转化为经验。震惊是一种最重要的现代性体验,同时也是现代美学最重要的特征。小说在叙事层面上写了冲突的解决和问题的掩盖,产生了虚惊的叙事效果;但将问题在意义层面的凸显,却使人产生了震惊的效果。小说对意义闭合的搁置,是对读者参与到一种意义拷问中的邀请。这一邀请也使《陆地行舟》进入到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之中。
这样将问题的解决搁置的叙事,与马尔库塞所批判的“肯定性文化”不同。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一书中提出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其否定性,《陆地行舟》叙事所带来的并非“升华”,而是“压抑”的效果。而只有压抑才能保存马尔库塞所说的“解放”的需要。
詹姆逊认为:“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陈宏伟也在小说《陆地行舟》中体现了对两个主要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通过书写以主人公为代表的科层制人员自我的分裂与认同的危机,以及自我理性化的努力与最终的异化,呈现了对科层制人员以及理性制度的反讽与反思;通过社会控制的多样性表现,也书写了弱者争取承认的斗争的必然性与复杂性。而权力的流动与弱者身份的流动,使社会冲突也变得复杂。而作者在小说中对种种冲突和其解决方式的揭示,也体现出作者的态度,即:冲突和矛盾不应被掩盖,而是要给予解决。这种对公共议题的深入思考与介入式呈现也反映了作者文学书写公共化的努力。
所以小说的调性是反讽与悲悯的共存,是两者的复调式呈现。在这种复调式书写中,小说呈现了其否定性的等等诸多特征,从中可见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这种饱含压抑的审美体验,却能够带给读者反思的动力。同时,小说也暗含着一种解构的策略,郁洋只能在一个反讽的位置上确立自己的存在,而这样的存在,就是荒诞的存在。在现代文学理论中,荒诞就是无意义。小说拒绝意义的封闭,一方面是对读者反思的邀请,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是在引入无意义的炸弹,炸毁社会系统给每个角色所提供的“庞大的‘自欺设备’”。[[[] 彼得·L.伯格: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65.]]对这种给定意义的拒绝和消解,也为马尔库塞所说的解放预留了可能。这显示了小说作为一种否定性艺术的价值,而这进一步增加了小说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陆地行舟》由三个中篇小说组成,以“精准扶贫”为题材,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扶贫工作要解决的是中国农村根深蒂固的问题——穷困、落后、愚昧等痼疾,只有亲历扶贫一线的人才能对贫困地区的真实面貌生发最真切的感触,才能认识到扶贫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和必要性。陈宏伟在创作谈中提到他有过一线扶贫的经历,或许正是作为“当局者”和“观察者”的双重体验让他有意识地选择了一种问题视角来呈现扶贫故事。值得注意的是陈宏伟的写作回避了宏大叙事策略,重心没有落在讲述轰轰烈烈、艰难曲折的扶贫故事,也不致力于对扶贫问题开出文学的“药方”,而是始终围绕人、指向人,侧重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关注在扶贫话语下基层干部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书写人物在重压之下如何辗转腾挪坚守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更可贵的是对落后乡村中普通百姓个体精神世界的关注,突出表现了作者的悲悯意识。本文试图通过对双重故事空间、隐喻主题和个体生命关注三个方面对以上观点进行解析。

《陆地行舟》的三个篇章均在两个故事空间展开:官场与民间,或者说城市与农村,具体指淮城的各级政府机关和贫困县村。社会空间的有意区分使扶贫工作中的两个主体对象更加明晰。叙事在两个空间来回切换,呈现人物不同的状态。在机关内部的叙事以心理描写为主,展现了焦灼、紧张的官场情状。《陆地行舟》中地方史志编委署名问题、《台风过境》中检查组胡组长的丢包事件、《镜中之舞》中微信工作群此起彼伏的紧急情况等情节以丝丝入扣的描写和强烈的现实感渲染着机关工作的复杂、繁重以及各级干部谨慎、隐忍的心理。文本中有两处心理描写点出了官场环境和身处其中的官员精神状况的关联:一处是会场上徐主任滴水不漏的话语使郁洋联想到了机关就像一个永恒的幽暗未明的世界,另一处是胡组长讲话后,郁洋透过油腻不堪的眼镜片看到眼前的世界混沌不清。“幽暗不明”、“混沌”既是郁洋对官场感性认知,也折射着他身处漩涡之中的存在焦虑。“油腻不堪的眼镜片”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叩击着我们的注意力。“油腻不堪”一词与詹姆斯•伍德所指称的“自由间接体”类似,使人物和作者的视角在文本中同时显现,表露着作者融入角色叙述的努力。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细节,“把抽象的东西引向自身,并且用一种触手可及的感觉消除了抽象,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它本身的具体情况。”被放大的细节与人物紧张、焦虑的内心相适应,对扶贫干部自身艰难性有意识的书写从侧面反映了扶贫工作的艰巨和繁重。当叙事转换到乡村时则以强故事性为特征,表现为以切片手法,截取并放大典型人物的典型故事。平时只会咧嘴傻笑的张根财也有复杂的心思,故意向郁洋隐瞒了种西瓜地的事实,想以此多换取扶贫的好处;来领奶粉的妇女一面拿着奶粉,一面恶狠狠地抱怨扶贫干部的“别有用心”;因为隐私被曝光,李道顺对扶贫干部大打出手;为了一座私建庙宇的赔偿问题,马忠良一意孤行拒不搬迁。一系列突发事件将人物的固执、粗鲁、愚钝、狡黠刻画得淋漓尽致,写出了看似简单的农民在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性。
扶贫这个词语本身凸显的是行为和对象的单一性,是在经济、文化等层面具有现代性优势的“城市”对处于劣势的“农村”和“村民”的帮助。但是在现实中情况是否如此绝对?面对城乡差异,扶贫干部应该以何种心态开展工作?作者在小说中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思考。朱主任与钱支书发生争执时,妇女主任及时化解尴尬,郁洋不敢去面对孙连发的家人,只好求助于妇女主任帮忙完成工作,“妇女主任”所代表的乡村内部力量无疑对扶贫工作顺利开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穿着风衣、戴着呢子帽的朱主任以一副城里人的光鲜装扮去马鞍村送进口奶粉,本以为很有面子,却在村里和村民发生争执。朱主任的呢子帽被李道顺踢飞在水坑中,被泥污的帽子代表的城市符号优势消失殆尽。他确实有心想把扶贫工作做好,但没有从思想上重视农民问题的深层心理原因,才会随意对李道顺许下无法实现的诺言,又随口说出李道顺百般隐瞒的隐私。朱主任和郁洋的受挫代表着陈宏伟对城市和乡村、官方和民间在扶贫话语中关系的深入思考。“很大程度上,贫困的客观存在,与‘精准扶贫’,其实可以被看做是一件事物的一体两面。”[ ]扶贫,不仅仅是城市话语对乡村的颠覆,不仅仅是城市去改造乡村,更需要从心态上去理解,去贴近,需要乡村内部力量的合作。在这样的思考中,作者所提出的“农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的观点就有了更深邃的思想力。
文本三个篇章命题均包含有强烈的隐喻意味,作者曾坦承这其中的艺术密码并不难破解。究其原因,与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写实性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这看似简单的“艺术密码”自然而然地嵌入故事主题之中,在充满隐喻性的叙事策略下使故事内部的复杂性得以有效呈现。以“陆地行舟”一语为例,《论语•宪问》中鲁国负责开城门的人将孔子称为 “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以此来形容孔子的理想信念,而小说中“陆地行舟”一词以背离现实的行为隐喻迎难而上的理想主义色彩,与儒家的这一精神无疑有着相似的内涵。朱主任在观鱼山庄题字“陆地行舟”既是应景之词,也是对马鞍村扶贫之行见闻和当下心态的总结。作者巧妙地安排朱主任题字点出了扶贫所需要的精神,却没有放任故事顺着惯性向下滑行,没有在下文以朱主任为核心展开扶贫工作描写,而是交待了在经历两场风波打击之后朱主任的决心熄灭了。这样的起落转折情节搭建下,能够多次顶住挫折和重压的郁洋所具有的理想主义者色彩就不言自明了。
事实上,作者在叙述中似乎无意将“理想主义者”的头衔郑重地戴在郁洋的头上,反而多次突出了他的失败:串珠子项目发生意外、主管的扶贫工作排名倒数第二、马忠良反悔拒绝搬迁、蓄水塔被盗,但是在这些失败背后,在对现实困窘的讲述中,暗含着郁洋精神成长的轨迹,而在困境和迷茫中的坚持更显宝贵,作为扶贫干部的担当、作为在这份坚持中得到了强化、丰富。当我们将郁洋的一系列失败放在现实中去考察,其实也正是对以郁洋为代表的扶贫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从捉襟见肘到沉稳果断的成长书写。
当然,小说的叙事也存在一个具有典型意味的问题。《镜中之舞》意在借胡衣一“对镜独舞”的自我表演和扶贫工作中“表演式”扶贫形成有意味的暗示对照,增强文本的艺术性、可读性。尽管这个目的在一定程度达成了,然而由于作者以完全外部的、有限的叙述视角来描写胡衣一,深层次的心理活动几乎没有涉及,导致了写作的“物态化”。作者有意将胡衣一塑造为“心有高山丘壑、绝壁深渊”的“女神”形象,但同时又赋予了她难以调和的矛盾性,外部的、公开的胡衣一和私人生活中的胡衣一形成了反差对照,神秘、光鲜和混乱、难堪的特质同时出现。人物的矛盾性由于缺乏细致的心理描写而难以自洽,造成人物形象的僵硬和分裂。这个问题实际上也代表着扶贫话语下现实主义写作一种困境,如何处理好扶贫小说的写实性与虚构性,如何拓展紧贴现实生活的扶贫题材的写作空间,使文本保持高度的文学性,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陆地行舟》的特质之一是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和对人物行为背后心理动机的谱写。陈宏伟在创作谈中讲到:“我相信小说的目标在于呈现精准的生活描述”,这样的写作态度从根源上避免了创作者高高在上的俯视姿态,日常生活的戏剧性情节服务于人物特征的塑造,而非供读者消遣。无论是官员还是贫困群众,作者都将笔触对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或批判或同情,在对问题的书写中表现着对个体精神的关注。
故事的主要人物郁洋有一套自己的官场庸俗生存法则,但是当他把“做最好的自己”的具体理解落脚在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时,也就找到了摆脱精神上虚无的方法。而在现实中郁洋也确实在和“虚无”作斗争。在形容帮扶对象张根财时,郁洋用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形容——“贫困户张根才就好比一个样本,是他深入扶贫一线的隐秘据点”。但是从情理上说,这个由扶贫办主任负责的扶贫对象是不可能具有隐秘性的(后文当郁洋路过村部的时候特意去绕一趟,想让村干部知道自己去走访贫困户的举动即是一种主动暴露行为)。所谓“隐秘”明显带有郁洋个人的心理色彩投射,因此这个与现实充满矛盾性的词语构成了打开人物内心的一个开关。郁洋选择保留张根财这个扶贫对象的原因是想在这里寻找一种真正“在场”的感觉,以这种真实感对抗扶贫工作中不得已的浮于表面的状态,完成对自己心理的调和,所以,真正“隐秘”的不是张根才,反而是郁洋内心深处对于理想信念的执着坚守。与郁洋坚守信念的“理想主义者”形象相对,李北亚和连瑞表现出精神的缺失或幻灭。文化局局长李北亚是官场“老油条”,有一套自己的官场生存手段,凭着几分聪明在真假之间游走,在危机来临时惯会混淆是非,趋利避害,尤其是胡衣一和连瑞事件的处理方式更是充满讽刺性。李北亚始终带着让人看不透的面具,在工作中处于一种表演的状态,而沉溺于自我表演的背后是真实自我的迷失。在官员身份之外,李北亚也是大学里出来的高材生,能指出辞书里的细微错误,这样一个聪明人发展到在现实中指鹿为马的境况,不禁让人唏嘘其人格、精神的衰微。驻村第一书记连瑞在扶贫岗位上一干就是两年,为当地做了一些实事,但对于职位提拔的期望成为他心中的执念,渐渐困于个人得失,虚浮的思想动机使他既不能踏实于眼前的工作,又希冀着不切实际的提拔,已然在怨愤中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引入对李北亚和连瑞两个人物的描写可以看做是作者对当下扶贫干部中存在精神缺失现象和原因的审视、反思。从表面上看,揭示扶贫过程中的问题是“逆创作潮流而动”,但从推动精准扶贫的健康发展层面看,其指向与颂扬精准扶贫的成就殊途同归。[ ]另一方面,在聚焦扶贫干部精神状态的同时,作者也关注到农民被贫穷遮蔽的个体心灵,关心他们内心的痛苦和诉求。村民马忠良在倒塌的蛇王庙旧址上重盖了一座新庙,而花费两周时间盖起的新庙在短短两天后又将被强拆。面对马忠良的荒唐举动,郁洋没有直接去指责他的固执、自私和对扶贫干部的不信任,而是“心中泛起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悲伤”。这悲伤是郁洋——也是作者——对马忠良孤傲、决绝行为的同情与悲悯,源自对马忠良作为弱小个体的理解。简陋、粗粝的蛇王庙所代表的痛苦与马忠良家里艳丽的紫薇花、整齐有序的小家庭生活环境形成了微妙的对照,巨大的落差和无意义的坚持使马忠良的痛苦与决绝显得真切、尖锐,蛇王庙的尖顶在阳光下闪耀,犹如他尖锐的痛苦无处安放。落后的、不合理的事物固然会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被淘汰、被清除,但不代表痛苦的意义可以自动消失,作家以悲悯之心将这份意义存放在文字间,记录一线扶贫干部面临的复杂问题和农村转型中普通百姓所承受的重压和付出的牺牲,抚慰他们的内心和灵魂。
《陆地行舟》最突出的特色在于陈宏伟在扶贫题材的限定下找到了自己的故事主题和叙述方式。一线扶贫工作经历无疑使陈宏伟积淀了深厚的责任意识和问题意识,表现在创作中即是自觉与社会发展相呼应,关注扶贫工作,关注扶贫干部和贫困群众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另一方面,由于作家坚持从实际出发,在真实反映扶贫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上,在对人物精神的分析、批判上表现出诚恳的态度和直面现实的文学精神。

我计划写一个扶贫题材的中篇三部曲,篇名分别叫《陆地行舟》《台风过境》《镜中之舞》。一个评论家朋友听说了连连摇头,他说太贴近现实的主题对小说创作极为不利。因为即使不看,也大概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他说小说需要飞翔,需要从现实世界腾空而起,如同山野的雄鹰。而像“扶贫”这类贴近时政的故事,如同扎根于田野的藤蔓植物,别说飞了,站都站不起来。记住,写小说要寻找梦想中的好故事。朋友的话令我犹疑,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第三部迟迟没有完稿。
朋友的话没错,但我心里终究不甘。谈到文学的当代性,说的是作品总要依赖于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状态,完全独立于时代的作品是不存在的。况且许多文学大师的作品也是借时代之力,然而无论放在什么时候去阅读,其艺术和情感的力量都历久弥新。可见,强烈地关注现实与优秀作品并不矛盾,并不会对小说不利。怕只怕,我们的写作是否真的具有当代性,是否真的呈现这个时代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我在自我怀疑与自我肯定相交织的矛盾情绪中写完了《台风过境》。
我的确在底层机关参与过两年扶贫工作,经历的生活感受颇为复杂沉重,这更加让我认识到,“扶贫”作为基层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得太少了,近乎被文学界无视。这岂不也是不正常的?为此,就算这个题材对小说再不利,我愿意正视它一次,哪怕最终归于失败。很显然,台风过境是一个隐喻,它包含的艺术密码非常简单。但是现实世界的山川、河流、温度和湿度,人物的样貌、脾气和情绪我又觉得很难用一个隐喻去表述,那是一种不可言传的意境,写作的时候我沉醉其中,甚至将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相混淆。我力图写出真正贴近现实的小说,不要飞翔,如果是藤蔓植物,就将根系扎得深一点,再深一点。
贴近当下生活的现实主义仿佛很容易被人看低,被认为是生活的复制或翻板。我觉得这不是现实主义的问题,而是我们拿司空见惯的故事,或者简单的、不现实的虚构来冒充现实主义。真正的现实主义具有生活表象所没有的复杂质感。我相信小说的目标在于呈现精准的生活描述,如同我曾经从事的精准扶贫一样。
原载2022年第12期《快乐阅读》。

